在古意中漫游
我认识丁中唐先生,可以用“很久”来形容。那时,我们同在教育系统,他是学校的一个主任,我是一个小记者,常随人“潜入”他的校园。
我们有时见面,有时不见面。见面的时候,他大多要陪我们吃饭,不见面的时候,我也总能想到他。想到他敦厚身影中悄然的奉献,想到他清澄的眼神里深情的表达,也想到他在沙渠的夜市上,握着酒杯那逼人的气势。
有句话说,杯中乾坤大,壶里日月长。他那么年轻,相逢朋友能“斗酒”,把友情的刻度,直接深化了出来,是多么好的事情。不像我一样,喝不了多少,看着大战的样子,一味地退缩,早早就做了逃兵。
酒喝着喝着,丁中唐就喝出了浓情,喝出了诗歌,而且竟然全是“古”的,这让我相当吃惊。“习习风送爽,郁郁柳丝垂。漠漠平湖上,翩翩燕子飞。”相处那么多年,我当初是不知道他写诗的。他的专业是英语,怎么能和文学“挂钩”呢?
更重要的,我们后来是本科同学,那么多人,更多的谈的是教书育人。丁中唐心中的文学梦想,是以业余的方式追逐的。我想到了大海,真正的勇猛者,是不轻易浮到水面的。他大概是淡于发表,也可能是投身教育,愈来愈忙,而不想过早地卷入文学的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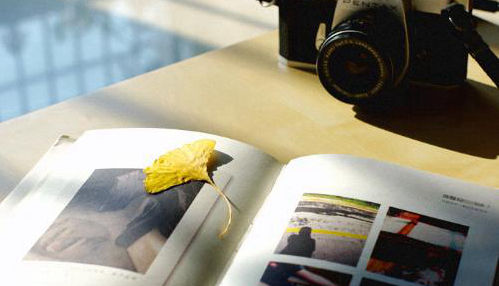
喝着喝着,他的诗兴,自己还是按捺不住了。往往就是这样的,最好的药材,不论深藏怎样的大山,总要被人挖出。我也惊讶他的诗歌的药材是那样的广阔,遍布神木,不论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不论是自然景观,还是历史景观,都在他的眼中,都在他的心里,都在他的笔下,把神木的古今变化写得那样有情有义。
他的诗歌触角发达,一部分笔墨,漫过故乡,挥毫在陕北。黄土高原因他的诗情,更加俊俏了,更显灵性了。在古意中漫游,他吟诵出更多的现实色彩,把陕北的身姿描摹得壮美极了。
太白山有诗:“抛笔飞砚入云端,留下千古泼墨痕。”丁中唐的墨痕也有不少,不仅在陕北,还在祖国处处。立意的精准、情感的浓郁、想象的丰富,他呈现给我们的祖国充满生机,是有滋有味的那种,让我们在荣光中体味幸福。
登山、登楼、登峰……登高是古代文人的心性,李白的《望天门山》、杜甫的《望岳》、苏轼的《题西林壁》,不仅是身体的抵达,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塑造,也因之更多的时候,成为他们一生当中作品中的标高。丁中唐登龙眼山,登文笔塔,登八达岭,他不辞劳苦地登过全国的很多地方,更多的时候,他身在校园,作为掌门人的他,内心的力量,蓬勃中的那种生命之火,和他往昔的游走是分不开的。
但他抒写最多的还是家乡的杨家城,他一次次登临,心灵的撞击一次比一次猛烈,饱含深情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而今只见残垣上,一片闲云向晚游。”他诗人的担当,内心的呼告,终于有了回应,杨家城“三地目标”,旅游高地、祭拜圣地、爱国基地正在建设的途中。
他无疑是一个朝拜者,不论疾徐,信念在心中,欢愉地融入自然,像泥土一样呼吸,在静谧中交谈,“恰恰鸟声闻,空山草木欣。登高须缓步,终作顶峰人”。
谁不想做顶峰人呢?我看出了丁中唐的心性,奋进中面显平和,隐忍里深藏力量,“红尘半百当泊淡,吟就新词润杜康”,多么好哇,在古意中漫游,漫游出一种优雅的生活,在历史中回溯,从现实里观照,总能给我们一种提醒。
玉平的玉
乡下人的名字,含有“玉”字的不多,男孩子就更少了,尤其在流行收音机的那个年代里。
可我的婶娘,给她的最小的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玉平。玉平,在我们村姓折的男孩子,只有他一个是带“玉”的。“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一个“玉”字,把乡村激活了,让少雨的村子润泽了、灵妙了、神气了。
我常夸赞玉平,有了你,草木就不是草木了。
“那是什么?”
“草木就变成草人了。”
“草人是什么?”他村小念过书,大约还不能够明白。
“在草窝里,我们都在草窝里,是不是?我们乡下人。”

“噢!我们走在草路上……”
我一下感到玉平有了文化,仿佛天边飘来小水珠,飞进他的眼睛,一点一点的光芒出来了。
“有了你,崖就不是石了,石就不是石了?”
“有刚哥,不是石是什么?”他又歪了一下头问我。
“是玉,你名字里的玉。”
“有这么神奇吗?”他略迟疑着。
“只要你常想着,就有了。”我的话,如是嵌入他突皱的额头间。
从不想着的玉平,或者常想着的玉平,身上是不佩戴玉的。但我觉得,他不过半百的人生,和玉是多么的相同。
玉平是祥美的,直直的个头,进门是要低头的,把谦恭自然藏入了。他也清瘦,仿佛少了一点气势,但根本不失亲和。他常来我住的小区,但一般是不找我的。他是去看前排的岳母。遇上我,声音拔高了,像他的个子。进去我耳廓的“有刚哥”三个字,塞满乡音,似大雨滴敲地,溅起的土气,都撞入我的鼻孔。我老远看见他,“刷刷”地走着,步幅是我赶不上的,在春节、鬼节、乡戏时,拿着酒瓶,对着村人盈盈地笑着。有时也见他,像火炉的天气里,他在老家的大门洞里,坐着小木凳,围坐在小桌旁,似乎在说着什么。
玉平是信义的,令我常想到一个词:玉章。落印为信,多少情谊尽在其中。我还想到了玉言、玉颜、玉树、玉盘、玉壶……想到了王昌龄,把大唐的盛情,隆隆地搬到了今天。“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他纯朴,像乡下的无声的植物,只有风,帮他说着话。他也像把根扎入节令的庄稼,借着雨,悄悄地拔节。我从未听到他有啥高言,但也见过他直来直去的,恍若在论理。情谊的道路拓宽了,一条条、一弯弯、一坡坡,他不论和人是怎样地交往,总是那样的义合。
玉平是坚守的,直视着前方,定定的,从未退缩过。在通往丰裕的路上,是一种无形的琢玉修心,那种看不见的玉的匠心,常让我感怀。他是一个劳动者,没登上领奖台,但他在我们心中,同样是一个“模范”。他没有停下来,不论在建筑工地上,不论在育苗的林地里,还是在准备炼铁开路的推土机旁,他都是坚守着,不灭的信念,在他的粗糙的手里紧攥着。
遗憾的是,他已松开了手,把人间的一切,都撒下了。我和村里人看他,他已永远地躺入院外的“小木屋”里,只有他的遗像,挂在了帐篷,有点模糊,像奔忙的岁月。我看见了婶娘,坐在沙发上,神情呆呆的,想必泪一定流在心里。我知道她放不下玉平,总说侯儿子在城里,还没有房子。
“她是怎么知道的?”我手指了一下。
“开始不知道,把她寻回来,看见帐篷了,她走过去,看见是玉平,跪下大嚎起来了……”玉平的妻子应着。
因了文代会,我不便参加玉平的葬礼,但那天上午,我想起了玉平,想起了玉平的“玉”,想起像玉的人,心里不由自主地翻涌着什么。
心里还有一种声音,就是送别玉平“呜哇”的唢呐声。
两个银圆
“以前两个坐在沙发上,一对对嘛,现在留下大大(陕北方言,指父亲)一个了。”哥哥噙着泪花,打湿的往事,一点点从眼眶溢出。
包产到户,人们的激情,仿佛除夕夜的火塔。春天钻出水嫩嫩的叶子,我的哥哥也舒展着向上的“枝条”,“茁壮”中成了乡亲们叫响的一个木匠。
“这个是给妈妈的,剩下的一个是给大大的。”哥哥指着他手上的两个银圆,声音着了铅似的,磕绊在唇上。我懵住了,不知拿这个要做什么。
“妈妈已不在了,怎么会收呢?”
“一会儿就要入殓了,这个钱要放在她口里。”
“噢!口含钱。”
如梦初醒,我一下想到陕北的乡俗,想到一辈子与土地相伴的母亲,想到她一生夹在紧巴巴日子里,从鸡鸣中转身,是那样的烦难。
哥哥学堂上得少,从我记事时起,他就在生产队里。学门手艺,是他走出田地的可喜的一步。走村串户,煤油灯下歇脚,那些来路不明的书籍,他大概看了不少。“嘴里放钱,让死者在阴间,不向阎王告状。”他说这个是假的,没有根据的,就是不放这个,妈妈也不会告状的,一辈子和善的她,路上路下和村人们拉个话,声调也没有高过。
“冥河有船,亡灵渡河,会付钱给摆渡人,这种说法有根据吗?”一个曾念过两月冬书的乡亲,接连揉搓着手,心急火燎地问。
“这个可能是传说,神神秘秘哟,十分吸引人的。”
“但没有钱,怎么能渡河呢?河不渡不行吧……”
我没想到深居乡下的哥哥,对民间的说法,有如此缜密的思考。
“过了河,船费是要付清的,不然,就会找子孙后辈的麻烦。”
“不会的,不会的!妈妈人品那样好,一辈子从没和村人红过脸。这样的好人,船费应该是免除的。”
哥哥接着我的话:“应该,应该!”
“至于银圆,放入口里,是因人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寿衣上没有兜,那个就是亲人的礼物;银圆圆圆的,像一轮乡间的明月,是不是代表着思念!”在我的低语中,泪水遮盖了哥哥的脸,阳光走过来,粗糙不见了,是那样的亮堂。
“哪里搞到的这个?”一个银圆,在我手心里平躺着,光溜溜的,头像是凝定的神情,另一个翻跳了两下,在我的掌心里,麦穗捧着“壹圆”,似乎在倾吐着什么。
哥哥说:“这个东西,我保存了三十多年,就是准备给咱老人用了。”他说做了三年学徒,自己成了师傅,到庙洼村给人做门窗,一个多月下来,活完了,过年还给不了工费。那家人有了变故,叫他先拿上两个银圆。回到家里,他从怀里掏出来宝物,父母暖心地说,当匠人还能挣来“洋钱”,你给咱们“保存”着。至于那户人家欠的钱,老伴被病痛纠缠着,吃上了救济粮。生活就像个无形的募捐箱,他也就算悄悄“捐赠”了。
我看着哥哥的脸,就见一个年轻的木匠,拿着凿子,不停地凿着。“咚、咚、咚。”从这一家,到那一户。他把清瘦的时光,凿成从一而终的老实的脸庞。而今他皱着眉头,眼睛每眨一下,都是对母亲的不舍。他还不止一遍地说:“我没把妈妈照顾好。”其实这些年,他一直陪在老人的身边,孝心向乡亲的窑面攀缘。在心灵深处,他是一个拥戴亲情的有力凿刻者。
请医生回老家,给母亲治疗,还不见好转,哥哥们火速将母亲转入城里。也许,一个人告别人世,医院是提前的送别者。黎明时分,已经没有意识的母亲,被全家人守护着,离开医院,回到老家的炕上。三个多小时,氧气袋瘪了,液体跟着停下步来,摘下面部的罩子,母亲竟慢慢恢复了点意识,眼神变得澄澈了,不时地转着。侄儿说:“侯大(陕北方言,指排行最小的叔父),你看,我娘娘(陕北方言,指奶奶)看你了……”我立即贴近母亲的脸,一声一声轻喊:“妈——妈——”母亲微弱地颤动着下颌,说不出话来,眼里溢着泪水。一会儿,听不到母亲的鼻吸,老去的时光,疲惫地遮住了她的双眼。
安放进棺里,辛劳一生的母亲,像往常睡着了一样。哥哥把银圆放进去,轻扶了母亲的下巴,嘴合上了,围在边上的亲人又发出一阵哀嚎。盖棺的那一刻,我想就要和母亲永别了,那个背我的人走了。
“留下的那个银圆,你保存好!”
哥哥揉着泪眼说:“一定,一定!”
我坐过的三种车
正值青春时,我坐的是卧铺车。和师范的老师相随,从榆林出发,坐在后大座上,塞了五个人。
像把人装进了布袋,车门“哐啷”一关,就相当于用绳子紧紧挣住了口子。没有窗子,但是有玻璃的,整个都封闭了,再怎么晴的天,从里看出去,都是灰褐色的。如果是黄昏,有一些分辨力,那车里就更是夜半了。
人都躺下了,没有一个空位子。像要被挤瘪的样子,两个过道,在叹着粗气,仿佛在“唉——”着,歪着身影的行囊,行囊和行囊间,夹着的,那是晃悠的小马扎。
小马扎上,坐着一个一个人。不论怎么样,我感觉躺在那里,“待遇”应该是比坐着好的。
一路颠簸着,感觉像在深秋的乡里,人像豆子一样,在什么里跳着。跳着跳着,就跳出一顿过路饭,跳着跳着,就跳出了小偷。
那气味,我可以用“混合”来形容。似乎是有浓度的,有一种“稠”,在鼻孔,堵在那里。也像一块无形的抹布,贴上了面颊。那气味,是不怀好意的,似乎要成为人的附属物,才算达到了目的。
时光远去了,但窗外的风,“簌簌”的,又把我老师的衣服,送过来。窗玻璃上,他的西服,挂在那里,摇来晃去,竟变得“油腻”了。那时,“中年油腻男”还没成为流行语。
“还好,咱没被偷了就好。”他挤出了一丝笑容。
“咱是‘无产阶级’嘛。”
卧铺车,从神木到西安,从西安到神木,像个没有表情的搬运工,冷冰冰的,只有我下了车,站在街边,或行走在街上,我毫无夸张的,一张一翕着,那样,我才变成我了,我才回到我了。
回到我,身前和身后,总有那些卧铺车,总有一些不夷愉的事情,堵住去路似的。追逐文学梦,有时也是“险途”,在西安城东客运站,我躺在铺上,车已“轰隆隆”地响起了。
“买票,来买票。”
“我买过了嘛。”
“把你的票拿出来。”
“假的,假的。”
“买不买?不买就下去。”
我在极力辩解着,那人就扯住了我的衣领,挥起拳头,是要打的那种。我说还有事,不回了,灰溜溜地下了车,甚至不敢回头。
在西安,城东客运站,有若充满了诡计,把人“哄”上了车,就不管你要的下车点了。我要的是“神木”,越过子夜,可到了那个绥德,就不走半步了。你要求退票,是不可能的,你要求管住宿,更是不可能的。黑灯瞎火,你再说多了,就有几个痞子过来,哄抢你的东西,或者用武力“对待”了。
总有那些卧铺车,还不得不坐。时光像冰车,“呼噜噜”溜远,不肯再折返。那鱼尾钻入我的眼角,把沧桑送过来。从神木到石家庄,只能坐卧铺车。
“怎么还有这个车?”
我以为,这个像有罪的家伙,早已逃亡了。没想到,它又和我见面了。它更是老旧的身影,甚至比我还沧桑。但这次还是不同的,来与去,一半坐卧铺车,一半坐大巴车。一半的一半,把我也折腾得够呛。
大巴车,好不了多少,在我的一些磨白的岁月里,像卧铺车那样烦过我。从神木到榆林,从榆林到西安,从西安到神木,我把自己的身体,只好塞进被时空放大的“仓库”里。
这个仓库,和卧铺车一样,是有体味的。有多少不合适的东西,通过嘴进入了,通过鼻子进入了,通过眼睛进入了。毫无羞愧之心,它仍然在做着加法,化作各个病的因子,在人不觉察时,在人忘了是哪一段旅途时,才会显露“真面孔”。
大巴车上小偷是不少的,从神木到榆林,从榆林到神木,我见过了不少。有的人,很疲惫了,生活像辆摇摆车,他一下子就睡着了。我看见了小偷裤腰上的刀子、指缝间的刀片、手上的夹子,甚至胳膊上的衣服,那也不再是衣服。
那也不再是衣服,那有何用呢?
那是来遮人耳目的,是小偷至今沿用下来的一个作案工具。
“哼、哼、哼……”
看见小偷坐不住了,转移阵地,准备有不雅举动时,有胆大的人,假装嗓子不舒服,“哼”了几声。
也还有更巧妙的:“哎!师傅,慢一点,我晕车!”以惊醒那些昏睡者。
当然,更多的人,是不会发声的,看见了,也会把眼眯上的,心想:“只要不偷我就行。”
我一般是不晕车的,除了首次坐卧铺车,一下车吐了一口外,再没有吐,但坐大巴车,我没吐过一次,可那个刹车,快行急停,仿佛在刹那间,在肚子里取走什么。“太不舒服了。”我一遍一遍地说给自己。
不过,回想起我坐大巴车的经历,我的贡献,就是那些语气词、感叹词、象声词,是发挥了一些作用的。它可能没有吓唬住小偷,但那么多乘客,像嗅到了空气清新剂,忽地打两个喷嚏。
火车来了,“咔嚓咔嚓”着,从西安到了神木,而且还提着速。多么好啊!白天坐,那沿途的风景,还会飞入电影里,晚上坐,“咔嚓咔嚓”中,就进入了梦乡。在神木,有时在街上,会有堵车的时候,我总想,哪里都可以堵,但不要在汽车站旁边堵就好。
这些年,我常想的一个词:出租。
“人的生命,是不是租的母亲的?”
“水滴般的人生,是不是租的大海的?”
“房车,是不是租的大地的?”
“我坐着出租车,我的人生,是不是正在出租?”
是的,我正在出租着自己的人生,而且,我还给人家付着费,有时还是不情愿地付着费。我忙着,师傅似乎更忙一点,还未进入小街,就停下来:“你走两步吧,那里会堵车的。”要不,就是前面坐的这个人,还忙着去洗浴中心了。
更多的,出租车就是“招手停”了,我的人生,还不得不给那些招手的人“出租”,有时坐上了,有时问上几声,搞不好价,就干脆不坐了。我上师范时在榆林街,坐“招手停”,我忘了是多少钱,但肯定是便宜的,可能坐五十米,也可能坐百十米,嬉嬉笑笑,仿佛莲花池的水波,荡漾在我们的脸上。
过去,是要给现金的。上去一个人,下来两个人,时而上,时而下,师傅也有时是记不清收费的。我有一次,提前给了钱,他下车,又向我要钱,还说我是耍赖。至此,我再坐出租车,下了车才开始付钱,大家就都浪费一点时间吧。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是不得不一次次,把自己出租给自己。
现金,似乎要逃出人的视线,变成生活的一个秘密时,扫码开始了。可我坐的出租车,是愈发得少了。更多的时候,我是步行的,把一个正在探索的世界,用自己的脚,在不停地丈量着、思虑着、祝福着。
“嘀——”微信来了,我会边走边看,那脚步不能再慢了,可还会挨着了桥墩。“能撞到我,说明你已经走了无数里路。”那是一行粉笔字,扭着腰身,还带点稚趣。我拨开夜色,仿佛一个小学生,正给我提点。
“无数里路,啊——啊——”
我感觉像一个哲学家了。
梦 野曾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鲁迅文学院高研班进修。全国作代会代表、全国青创会代表。曾获柳青文学奖、《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曾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两次入选“陕西省优秀作家艺术家扶持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