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阵子,下雨或者刮风时,总有一个念头冒出来:母亲还没有回来。小时候,若母亲没有回来,天黑了也不许关门,就站在门口喊。如今,母亲再也不会回来,她沉寂于荒野之中,新鲜的土丘看上去有点儿突兀。不过,一年之后,小儿大喊:“爸爸,奶奶长草了!”是的,草芽冒了出来,像是母亲给了我们一个消息。
母亲去世这事,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像是松鼠找到了松子儿,它得找个地方藏着,不到万不得已,它不会去吃。假装母亲还活着,我好像还可以依偎,或者说搀扶,好像这样才心里踏实,才什么也不缺。
从前,每天开摄像头看母亲。很多时候,她坐在客厅的矮圈椅上,喝水、吃药。我喊一声“妈”,她抬起头,看着摄像头,应了。她问我吃早饭没有,冷不冷,热不热,我答了。我关掉麦克风,再看一会儿她,她还在盯着摄像头,总觉着那是个神奇的东西。
母亲中风之后,行动越发迟缓。慢慢起身,拄着拐杖,走来走去,她总是谢绝保姆的搀扶,谢绝保姆给她穿尿不湿,她想像个正常人那样。坚持了十来年,直到去世之前,她还是要夜半起来上厕所,她说醒着不起来解手,像是尿床。她不喜欢那个感觉。
我回家,保姆如遇大赦似的。我睡在母亲身边,照应她,扶她起床,给她穿衣服穿鞋。有一回母亲轻轻喊我,说我的肩膀露在被子外头,她想给拉一拉,可她翻不过身。有一天早上,母亲说她看见我的胡子有几根都白了,叹息怎么一转眼,当年那个光屁股的娃娃如今胡子都白了……她好像有点儿不信,我蹲下来给她提鞋子时,她伸手摸了摸我的下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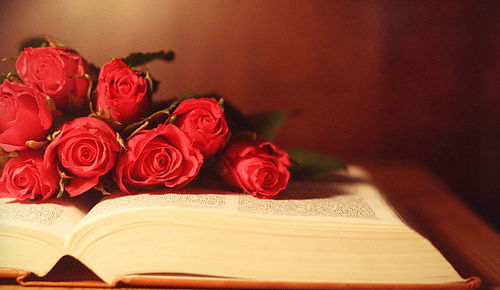
监控器可以存储30天的记录,多一天就会顶掉最早的一天,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消失,一个月之后,那里没有母亲了。
平常每年,总要回去几次看她,陪她。
如今也要回去,只是去母亲坟前看看,已长了草,开了野花。有时要焚香,有时只是看看,据说香是信使,不年不节的,让它给母亲送信,像是打扰。
悄悄叫一声“妈”,说:“我回来了。”走时,再喊一声:“妈,我走了。”母亲在时,她要送我,送我到公路边。后来搬去县城的第一年,她对新房还不熟,我要走时,母亲着急地问我,在哪儿才能看着我走。我领着她站在阳台上说:“这儿能看见。”“还有哪儿能看见?”母亲有些着急,我牵着她去了靠路边的窗户。然后,再出门。我站在楼下冲她招手,尽量走慢一点儿,让她能多看看我。“阳台上还没看呢!”我站在那儿,等着她出现在阳台上,然后再走,一点儿也不像演戏。
如今往返1000多里,只是在她坟前站一会儿。
“不要在我坟前哭泣,我不在这里。”这是很久之前的一首美国歌曲的歌词,听上去,总像是有别的事情发生,只是,我和母亲除了偶尔在梦里见一面,到底是永别了。
我想着带点儿母亲的遗物。
第一次带走的是母亲的老式针线夹子,里头夹了各种各样的鞋样儿,有大人的,有小孩的,有敞口的、松紧的,有低沿棉鞋的。一张一张看过去,好像母亲正在纳鞋底,针有点涩,缝之前她要在头发上划一下……里头还藏有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是年轻时的外爷。
第二次带走的是母亲的一把梳子,上头有她的一根头发。
这两天无意间看到一本薄薄的《我如何清空父母的家》,是比利时一位女作家写的一本小书。
她是独生女,父母离去之后,她回到家里,也可以说回到他们中间,看见父母的情书、饼干盒子、小椅子和写有字的餐巾纸—那是母亲的字迹:1983年3月2日,闲谈馆,奥尔良;1983年6月18日,布鲁日,抒情酒馆……
那些有点陌生的地名、陌生的桌椅,坐过她相对年轻的父母,那时他们说话,或者喝酒,或者吵架,活生生的,生动而细微。不像如今这般空寂,空气里似乎还有他们的气息,其实已经天人永隔。
她写道,在父母离世后,有那么一刻会萌生出一种莫名的解脱感,羽翼顿然一轻,天地我独翔。但片刻之后,虚幻的自由让人虚脱,一转头又见到父母亲的遗物,那沉甸甸的包袱的重量便统统回来了。
这样的感触我也有,母亲的遗物,除了几个陪嫁的木箱,就是用了一辈子的桌椅、农具、厨具,剩下的只有针线和针线夹。我记得有一张她年轻时的相片,扎两条长辫子,只是怎么找也找不着了。
我将针线夹和梳子带到武汉。一个花样子,妹妹带到西安。弟弟带了几个盘子去了南京。

母亲好像被分成三份,各自完整,形成闭环。兄妹三人每人一个妈,我们带着她到处游荡。
我们啥也不缺,就是缺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