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起拉开窗帘,只见窗外的敖鲁古雅民俗村白茫茫一片,降雪了,这是今年根河的第一场雪,也是中国的第一场雪。
内蒙古的根河与黑龙江的漠河处在同一纬度上,都在大兴安岭中,都属于中国的北极。中国的极端寒冷天气,都在这两地产生。这两个县级市,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漠河处在北纬50度20分与52度33分之间;根河处在北纬50度20分与52度30分之间。从近年来测量的数据中,漠河的极端寒冷天气是零下52摄氏度,根河的极端寒冷天气则达到了零下58摄氏度。2018年,国家气象局便将根河命名为中国冷极。
处在同一纬度上,为何根河比漠河更冷呢?而且,漠河更靠北,从它的县城出发,向南三百公里才是根河市。照理说,应该漠河比根河更冷才对。为何恰恰相反呢?我想,不可忽略的是两个构成冷极的必然条件。第一,漠河的海拔只有六百米,而根河的海拔是一千米。漠河往北依然是隔着黑龙江的俄罗斯境内的外兴安岭;根河的北面却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山可以作为抵御寒流的屏障,而平原则是寒流过境的大通道。第二,中国的冬天来自北方,而让北方一夜入冬的,则是那永不爽约而人类穷其所有的智慧也无法阻拦的寒潮。气候决定了地理的作用,也决定人类生存的方式,甚至国家的兴衰、王朝的更替,都与气候的变化有关。这是一个宏大而且有趣的话题,在这里我不展开论述。还是言归正传说说寒潮吧。我们从小听广播的天气预报,总会听到“一股西伯利亚的寒潮正在侵入我国北部地区”这句话。如果说,寒潮的策源地是以格陵兰岛、北冰洋、北极苔原与泰加林带为核心的北极圈,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北极圈的寒流无法进入西欧,却涌向了位于它东南方向的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位于最广阔的亚洲大陆的腹地,高纬度的气旋以及陆海热力的差异在西伯利亚交汇,使之成为永久性冷高压的聚结地。来自格陵兰群岛的寒流在这里积蓄更大的能量之后,依然沿着它的轨迹向东南方向迁徙。而它的东南近邻便是中国、蒙古、哈萨克斯坦等亚洲国家。西伯利亚寒流进入中国,分东、中、西三路。东路是从西伯利亚东亚东部借道蒙古国东部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尔后取道华北地区南下;中路从西伯利亚中部过境蒙古国中部入境中国西部河套地区,尔后长驱直入华中地区;西路是从西伯利亚西部进入中国新疆,经河西走廊,像候鸟一样,飞向膏腴之地的东南诸省。历史记载,西伯利亚的东路寒流最为强劲,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便是自黑龙江伸延到内蒙古的大兴安岭地区。首当其冲的便是漠河与根河。因这寒流自东南来,位于正北的漠河,遭受的冲击力便没有根河那么猛烈。这就是根河为什么是中国极端低温天气纪录的保持者。
二

我是十月的最后一天,取道哈尔滨来到根河的。往常这个时节,哈尔滨应该已经进入冬季。可是今年,城市的公园里依旧绿树成荫,路边,赭黄的林叶犹如金箔在阳光下闪射炫目的光芒。而中原,特别是江南与岭南,气温较往年要高出许多。在北纬30度以北,这时应该到了“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季节,现在却仍然是暑气未消、花团锦簇,让人产生河山非复旧河山的感觉。
但是,过了嫩江平原进入大兴安岭,气温明显降低了。零度之下,站在阳光下也感觉不到温暖。大兴安岭是东北平原抵御寒潮的天然屏障。世界上有三个可称为黑土地的平原,东北平原是其中之一。另两个是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平原、乌克兰平原。黑土地平原的纬度通常是北纬45度至北纬50度之间,都是世界级的粮仓。拜大兴安岭所赐,东北平原才可称为黑土地。所以,要保护好东北大平原,首先要善待大兴安岭。
穿行在大兴安岭中,但见河山逶迤,路远林深。夏秋时节影响甚微的冻土路面,现在变成了陷阱或者坎坷。同行的根河籍的弟子对我说,往年这时候,大兴安岭已盖上了雪被子,今年冬天迟到了。
根河我去过几次,春天夏天秋天都去过,唯独冬天没来过。看到路边河中的流水还在欢快地流淌,心中不免怏怏,数千里赶来看一个根河的冬天,难道希望又要落空了?过牙克石,气温明显低了许多,冻土路面越来越多了,空气突然变脆了。弟子说,变脆的空气就是寒气。遥远的天空由湛蓝变成了铅灰。这是在酝酿一场暴风雪吗?弟子说:是的。在根河,汽车按一下喇叭,就会惊掉大片大片的雪花。这里的冬天长达半年,最奢侈也最无聊的就是雪。南方人把雪当作诗歌,而雪,却是我们的苦闷。
在一种等待与期盼中,在根河市住了一个晚上。其实,那夜的根河,放在中原,已是非常寒冷的天气了。零下8摄氏度,所有的村庄都变得萧瑟了,大地横陈的江河、林木、田野与山脉,都被寒气包裹着、蛰伏着,盼望三阳开泰的那一天。根河却不一样,这里的原住民觉得零下8摄氏度只是那种完全可以忽略的轻寒。根河的朋友们为我们举办了丰盛的晚宴。赴宴的路上,但见街上的每一间餐厅与超市,都是灯火通明,热气腾腾。他们对冬天不是服从而是顺应。寒冷没有让他们怨天尤人,而是用自己的酒,把一个又一个的冬天全都灌醉。
夜宴给我带来了好心情,一早起来,纷飞的大雪给了我一个期盼已久的黎明。一夜之间,气温降到了零下20摄氏度。我穿上早已备好的“加拿大鹅”,迫不及待走出了酒店,宿醉未醒的大街寂静无人。我看到路边的白桦林,灰白的躯干像一只只熄灭的蜡烛,不远处起伏的山峦上,那些茂密的落叶松与樟子松,披着冰晶与雪雾,无言而安静,仿佛一尊尊入定的头陀。我踽踽独行,仿佛走在安徒生的童话中。我甚至轻声念起李白的《北风行》:“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
朋友赶过来了,笑着说:“燕山雪花大如席,这太夸张了。燕山在中原边上,哪来那么大的雪?”我说:“你又没生在唐朝,怎么会知道当时燕山的气候呢?”地球的气候一直在演变,大冰河期、小冰河期,甚至寒潮期、暖湿期。变暖与变寒,可以预见但不可以改变。在屈原的诗歌中,荆楚大地上有成群结队的大象,有热带那样的大龟,现在还能看到吗?气候可以把一个地区变成热带,也可以变成寒带。这种变化,人类无法干涉,也不能参与,人类的改变只是小轮回,而气候的改变是宇宙的大轮回。
近些年,气候变暖似乎成为了趋势,而局部地区却变得更加严寒了。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沙漠上,唐代还非常浩瀚的居延海,宋代以后就日渐干涸了。现在,它重又变成了沙漠中的泽国。刘禹锡的诗“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他感慨人世变幻而山川依旧。其实,若从气象或地质时间看,山川也并非依旧。
雪不是在下,而是在涌。根河的第一场雪,显示出掀天揭地的气魄。现在我眼中看到的,既是北国冷极中的气象,也是天象、地象。
三
当然,我来根河的动机,除了感受这里的极端天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创作《忽必烈》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来这里考察蒙古民族的形成。
据《蒙古秘史》隐晦的记载,蒙古人最早的祖先是在种族战争中侥幸逃脱的两对夫妻。他们隐藏在大兴安岭的密林中,过着狩猎与游牧兼具的生活。他们在这片呵气成冰的山林中悄悄地繁衍,几个世纪之后,两对夫妻的后代终于变成一个部落。我想,这个部落不会太大,它甚至不会超过一千人。由于食品供给有限,加之极寒的天气导致人的生育能力的降低,游牧民族的人口远低于农耕民族人口的增长。
基于史料的分析,也基于对环境的判断,我认为最早的蒙古人发育于大兴安岭北麓及额尔古纳河之间,即今天的根河与额尔古纳。这两个地名是解放后产生的。之前,它们曾合起来共享一个名字:拉布大林。再往前,叫室韦县,再往前,这里没有名字。拉布大林是蒙古语“勒格塔林”的变音,翻译成汉语即小孤山。
大兴安岭众多峰头,这小孤山是哪一座呢?现在已泯不可考。根河最早的历史记载是在北魏,此前这里天荒地老,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政权。唐史书中,第一次出现了蒙兀室韦这个名字。史界认为,这是蒙古人最早的称呼。中唐之后的文献上,又把室韦称作“鞑靼”,这个鞑靼,后来又被称为契丹。俄语中的中国一词,即源于契丹,也可翻译成鞑靼。
一些史家认为,最早的蒙兀室韦是东胡的一支,因为室韦与鞑靼通假。但是,法国学者伯希和推测,室韦是“鲜卑”的同词异译。我对伯希和的推测表示赞同。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东胡,还是鲜卑,抑或鞑靼、契丹和蒙古,很难将他们进行民族的严格区分。古代民族战争的发动者,无不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抢占资源,二是掠夺人口。一个强悍的王,会使他的民族迅速壮大。一个王的溃败,他的民族及部落便会迅速变得弱小或者消亡。在这样一种历史趋势中,每一个族群的来源便会复杂。谁也不能保证他的族群是单一人种。也不能保证他的族群文化能够永远不走样地传承。所以,民族的强弱转换,草原霸主的崛起与陨落,便是一部融合与交汇、相斥与相吸的中华大历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命运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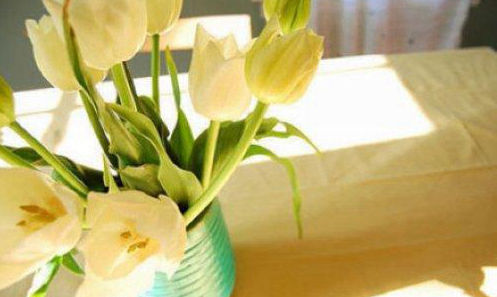
为什么说,蒙古族的祖先是鲜卑人呢?这与《蒙古秘史》的记载有关。那两对劫后余生的夫妻,应该是东胡为占领今呼伦贝尔地区对土著鲜卑人发动战争时的幸存者。从根河到蒙兀室韦这一片区域,森林与草原交织。现在,那里依然是中国乃至世界最美的草原。相信中世纪之前,那里的生态环境应该更好。
草原被强势的游牧民族占领,这两对战争的孑遗只能躲藏在深山老林。从森林走向草原,这不仅仅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强大。人力、物力、战力保证一个族群向资源更加丰富的地方流动。这是弱小的民族向往而不能实施的梦想。
在呼伦贝尔地区,强大的东胡向西迁徙,从那里进入河西走廊乃至新疆、西亚的丰草区;鲜卑向南迁徙,抵达大同建立了北魏政权,尔后挟雷带电南下洛阳建立都城,这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第一个中央政权。历史记载,当蒙兀室韦成为一个部落后,他们没有能力西迁或南下,只能沿着北纬50度的轨迹一路向北,最终抵达今蒙古国的斡难河畔。远离一切繁华,远离一切敌人,在那片土地上,真正的蒙古人的历史才正式拉开序幕,不同的是,他们没有从悠扬的牧歌走向更加悠扬的牧歌,而是从一片苦寒走向另一片更加凄厉的苦寒。
四
在根河,我看过鄂温克人住过的撮罗子,也见过古时原住民住过的地窨子。我不明白,撮罗子这种撑起来的尖顶圆棚子,如何能抵抗极端的寒冷,而地窨子则是半在地下,覆顶是树皮与兽皮,暴风雪中,地窨子可以生火取暖。现在,这两种土著的建筑都已没人居住了。根河的居民都住在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建筑中,九月份就开始供暖。我想,最初生活在这里的蒙古人,应该是夏天住在撮罗子里,雪天便在地窨子里猫冬。后来,牛皮和羊皮多了,他们便设计出蒙古包。这种易于迁徙的毡房,应该是撮罗子与地窨子的结合。从大兴安岭迁往漠北的蒙古人,他们的勒勒车上,必定带着蒙古包。如果说勒勒车是牧民的草原之舟,那么蒙古包就是草原上流动的城堡。
在北半球,存在着三种世界,即农耕世界、游牧世界与海洋世界。它们互相连属又互相抵御。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及生产方式,造就了三种文明。生活在不同文明中的族群之间,经常爆发战争。最早的战争是为争夺资源,后来添加了信仰。再以后,随着国家概念的出现,领土战争又随之出现。战争必有胜负,但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人类的战争几乎没有胜者。人类在衰落中进步,又在进步中衰落。每一次战争与缠斗,受伤的永远是人类自己,当然也涉及到自然。
近代以来,随着科技与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与扩大,农耕、游牧与海洋三种世界的边际逐渐模糊。但三种文明对不同族群的影响依然巨大。在北极文化圈中,曾经有两大民族一度成为了主宰世界的强大力量,他们一个是代表海洋文明的维京人,一个是代表草原文明的蒙古人。
在根河采风考察时,我一直在想,最初离开这片土地的蒙古人,是因为自然环境的改变还是族群残杀中的败者?蒙古人最初的图腾是苍狼与白鹿。在额尔古纳,我碰到一名苍老的马倌,他告诉我,有一只狼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叼走了他的一只马驹。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找到这只狼,并赤手空拳与这只凶猛的独狼搏斗了大半个夜晚,终于用半截马鞭将这只狼勒死。他娓娓道来,语气一点都不夸张,可是我却如同看了一部好莱坞的战争大片。他长得并不强壮,可是身上却体现出蒙古人的强壮与剽悍。
至今,在根河一带的大兴安岭中,苍狼与白鹿都还存在。狼是牛羊牲畜的敌人,而鹿则是驯兽中最可靠的运输英雄。极寒天气中,连烈马都要趴窝儿,要靠人们投喂干草活命,而鹿却可以踢开深达数尺的冰雪,找到贴地生长的苔藓为食。苔藓是鹿唯一的美味,它不假牧人的帮助,而是自己寻找。它既能拉爬犁、雪橇,也可以驮载物品。在勒勒车发明之前,鹿是牧人最好的脚夫。蒙古人选择苍狼与白鹿成为他们的图腾,这是一种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选择。苍狼会激发他们的斗志;而白鹿,则是他们忠诚的朋友,吉祥的诗意。二百年前,从根河到漠北,是同一片草原的两处风景。现在,却变成了两个国家的不同领地。但是,不管怎么说,从地理特征上,它们都属于蒙古高原。从气象特质讲,它们仍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极。
五
地理上的北极,是指北纬66度34分以北的广大区域。这片地区的总面积有2100万平方公里,人们习惯称这里为北极圈。北极圈国家有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丹麦、冰岛、挪威、瑞典、芬兰。这些国家我全都去过。除了荒野,它们的城市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的寒冷。根据历年的气象统计,世界上最冷的十个国家是:冰岛、俄罗斯、瑞典、加拿大、挪威、芬兰、蒙古、哈萨克斯坦、丹麦与爱沙尼亚。这些国家中,蒙古与哈萨克斯坦并不属于北极圈。可是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以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被称为世界上最冷的三个国家都城。为什么乌兰巴托与阿斯塔纳的寒冷超过北极圈中的国家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它们毗邻西伯利亚。世界上最冷的城市也不在北极圈,而是西伯利亚地区的雅库茨克,它的极限低温达到零下60摄氏度。不过,雅库茨克还不算世界上最冷的。同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一座只有五百人居住的伊米亚康,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71.2摄氏度。顺便说一句,寒冷并不可怕,伊米亚康小镇上的人口平均寿命达到了85岁。
从纬度上看,中国的漠河离西伯利亚最近,两者之间只隔了一条江,一道山,那江就是黑龙江,那山就是外兴安岭。以前,那条江与那条岭都是属于中国的。根河离西伯利亚稍稍远一点,但也远不了多少,也只是隔了一条江与一道岭,岭仍是外兴安岭,江是额尔古纳河,它是黑龙江的上游。在人类各种丰富而灿烂的语言中,汉语肯定是最优秀的语言之一。关于寒冷,汉语将其分为六个层次:轻寒、薄寒、小寒、大寒、苦寒、极寒。古人对气候的表述乃至二十四节气的划分,来自最初黄河中下游中原人的观察与经验。霜降带来轻寒,塞北可称为苦寒。三九天自冬至开始,大寒是一年中最冷的十天。在尧舜禹等伟大的先贤创立中华文明的初期,中原人的履迹无法抵达遥远的西北及东北边疆,那些地方是游牧民族的天下。以放牧为生的族群,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游牧在北极的边缘,如果一年的春夏有三个月,那便是游牧者的天堂。在苦寒与极寒中,他们无意创造史诗,但浩瀚的冰雪世界,却可以帮助他们提炼与储存创世的能量。
今年,根河的第一场雪来得稍迟,但迟来却没有缺失。弟子告诉我,山里的积雪已经很厚了,河水一夜封冻,虽然还不结实,但蓝莹莹的冰坂看上去也非常美。他问我,你愿意像古人那样,到山里去坐一次狗爬犁吗?我回答:当然想坐,我还想在地窨子里住一晚上呢。在地窨子中间烧上一堆篝火,搬来马奶子酒桶,一碗一碗喝到天明。沿着北极的边缘行走,享受着苦寒与极寒,也陶醉着中国最北的风景线,这是人生的快事、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