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哪一年,我与家人到余姚河姆渡遗址游玩。蓝天白云之下,天空似乎透射着远古的光线,长短不一的木桩在野外散乱竖立,它们似乎接近碳化,与我们在泥地上的人影一道,影子藏得短短的。河姆渡遗址是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远古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河姆渡镇河姆渡村的东北,我从家里出发,驾车两小时左右即可到达。由于路程不远,此后去过多次。第一次去时,像是进入附近的小村庄,随着遗址文化影响力增大,规模越来越宏伟。
我们观看了远古人类的栽培稻谷、木建筑、捕猎的野生动物、采集的植物果实和墓葬遗存,同时,看到一个不起眼的黑色陶钵复制品,以及许多由此衍生的工艺品,黑陶弧圆角长方形,平底,其貌不扬。1973年,这个黝黑的陶钵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真品目前藏于浙江博物馆。我并没有意识到,陶钵两侧刻着的类似野猪的图形,算得上是记录了中国人的养猪的开端,使得七八千年之后的人们发现,野猪向家猪过渡时期的形态特征大概如此。猪的头部低垂,长嘴向前伸出,双目圆睁,肚子微微鼓起,四足交替前行,尾巴下垂,鬃毛竖起。
野猪的战斗指数很高,猪的代表人物猪刚鬣在天上被称为天蓬元帅。《西游记》中,猪八戒与孙悟空从半夜打到天亮,煞是厉害。湖南博物馆有一件国宝,是商代青铜豕尊。这件被简称为猪尊的青铜雕塑,獠牙外露,双耳直立,鬃毛竖起,两眼睁圆,野性十足。
不管河姆渡黑陶猪姓“野”还是姓“家”,它的模样已经与现代家猪十分接近。由此,专家们推测,猪的驯化饲养历史,在中国至少已有七八千年。

有一个出自《后汉书·承宫传》的成语叫“牧豕听经”。汉朝时期,孤儿承宫靠给别人放牧猪羊为生。乡里徐子盛老师给学生讲解《春秋经》,承宫偷偷躲在教室的外面,边放猪边听老师讲解。还为师生捡柴草,想方设法让老师允许他进教室听课。比喻求学努力。
感受励志的同时,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养猪是穷人干的活。在古代确实如此,尽管肉食者鄙,但肉食者与牧豕者分属不同阶层。在相当长的时期,古人以食羊肉为主,然而,河姆渡时期以后,驯化养猪一直未曾停止。家庭散养,算得上是真正的养猪。七八千年饲养史,规模化养殖的历史简直不值一提。
黄地里和及周边小山村,至今还稳定地保持着饲养家猪的习惯。
散养家猪是一项考验韧力的长期工程。我的父母从青年到中年,直至耄耋之年,年复一年坚持这项伟大的事业。
人们印象中,猪堪称好吃懒做的典型代表。事实确实如此,一日三餐,餐餐不能少,饭来张口,养尊处优。而且食量极大,大大深深长长的猪槽,也许算得上天下第一号大碗。为它提供足够的食物,消耗了父母整年大量的精力和汗水。
它们懒得打理卫生,从来不介意在猪槽边拉屎拉尿。早年,勤劳的父母把收割完的所有稻草储存下来,定期铺在猪栏里。可总是赶不上猪的污染进度,因此,猪栏臭气熏天,污水横流。
次年春天,大地回暖,紫云英把田野打扮成紫白相间的童话世界,父母收割美丽的紫云英,源源不断地送进灰暗猪圈里,供家猪享受。不久,田里灌上春水,散落的紫云英花瓣,连同碧绿的茎叶被犁开的泥土覆盖,花瓣香,青草气,泥土味,随春水在田野荡漾开去。
种田了,首先给土地增加肥力。这个时节,整个小村开始弥漫浓重的猪粪味。家家户户把猪栏清空,一层层稻草,长时间浸润于猪尿猪屎,被勤劳的村民用五齿锄头挖掘出来,乌漆麻黑,陈腐的臭味浓得惊雷都打不开。
一个猪圈,贡献三十担黑暗料理不在话下。担子的底座仅仅三块条形木板足矣,上头两根竹板拗弯,塞得满满的,扁担吱嘎吱嘎,猪尿猪屎一路淋一路洒。田埂路被踩得面团一样软糯,一般人走上去把握不好重心,前俯后仰,老农民挑着担子,赤裸的双脚横向着地,左脚板烂泥右脚掌猪粪,健步如飞。
田里的土经过犁、撬、耙,已经软烂软烂,水刚好覆过泥土,一脚踩下去,深陷一个大坑,泥土从脚趾缝间爬上来,立刻把小腿包围拥抱。换只脚前进,随着把脚拔起,泥坑“吱嘎”叫起来,双脚轮换前进,脚底下“吱嘎吱嘎”,像有庞大的青蛙鸣叫着跟随。
这时,村民把担子卸下肩膀,置于水田中央,把猪粪倾倒出来,用手抓起猪粪,向远处抛撒。黑色的猪粪,随着村民一次次地扬手,啪嗒啪嗒落下来,溅起水花,均匀地铺在水田上。大批大批的蜻蜓围聚过来,在水田低空振动翅膀。
想必蒲松龄一定亲眼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否则,写不出这样的话:“棚中猪多,囷中米多,养猪乃种田之要务。”家猪对种田提供了主要的肥料,劳作的人不觉其臭,不嫌其脏。这并非“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而是劳动的味道昂扬在自然天地间。被公认为懒惰的猪,它们的排泄物,本受人掩鼻,却因为村民的劳动,成为环保绿色的有机肥。
少数家庭养母猪,母猪不能杀了吃,专门用来生产小猪。小猪长到三四十斤之后,附近村民便有人上门选购。东家定个日子,大家围在院子里,指指点点,不时用扫把赶一阵,对口草的好坏,个子的壮实,肉质的肥厚,见地深刻地评说一番。议论纷纷之后,各自把选中的小猪装到特制的竹笼里,过秤付钱,现场付不出的就赊账,然后怀着一年的希望抬回家伺候。遇到一头优秀的母猪不容易,要能吃能怀上能顺产能哺乳,农家看重家畜兴旺不亚于人丁兴旺,母猪要连续饲养和生产好多年。乡村信息传播很有效,如果买回去的小猪表现乖顺,长的大,第二年更多的顾客会争相上门。
遇到一头好的种猪更加不容易,一般方圆十几里,只有一两头种猪。我上小学时,时常遇到有人赶着种猪在路上行进,远远地一股骚味扑面而来。遇到有需要的,把它直接赶进猪栏,或者村民打开猪栏,母猪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根本不知道避嫌。于是,赶种猪的行当,常常成为乡间取笑的素材。如今不知为什么,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识过这样的场景了,也许母猪用不上种猪了?
家养的猪,大部分既不是母猪也不是种猪。如果是公猪,必须阉割。乡村的兽医都有一手熟练的阉割技术,青春期的公猪,被他们从下腹部取出宝贝,声嘶力竭的叫声中匆匆缝上几针,涂几下碘酒,然后让它们挣脱而走。殊不知,被阉割后,公猪力大豪勇的特征消失殆尽,只剩下懒惰安逸。正像自然科学家赫森所说:“猪不像马、牛、绵羊、山羊那样鲁莽,天不怕地不怕;不像鹅那样满怀敌意;不像猫那样屈尊俯就;也不像狗那样摇尾乞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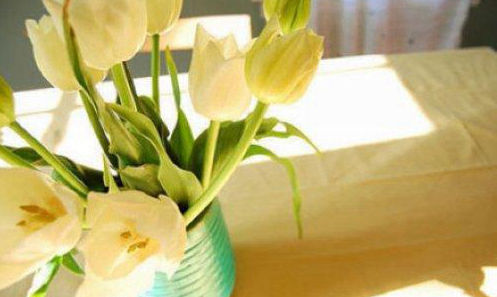
我跟父亲去卖过几次猪。当时政府规定,养大的猪必须卖给供销社下属的一个定点收购点。天蒙蒙亮,父母事先请好的邻居过来帮忙,把肥猪拖出来,架凌空称重量,然后绑在独轮车上。这时母亲总在一边手不知往哪放,嫁女儿一样兴奋和忧伤,看了秤,嫌自己养得太小,才两百七十斤啊?太不肯吃了!
然后,父亲让我坐在独轮车的另一侧。我的体重不够,父亲又搬上两块石头,这样,一边是养了一年的肥猪,一边是养了九年的我和历尽风雨的原始石块。
最难熬的时刻,是收购点收购工作人员的“判”。面对从附近各村排队而来的肥猪,工作人员用眼一瞥,开口一句“八刀”,就确定了大家眼巴巴一年的命运。判断的对象是猪的肥瘦,八刀就是打八折,九刀意味着打九折,这可相差不起,但是人人都没办法,只得听天由命。有人唉声叹气,有人喜笑颜开。
农民施肥的方式慢慢发生着变化。收割稻子之后,一些人把稻草切碎,撒回到田里,增强土地肥力。除了这,村里种田再也看不到自制有机肥了。从猪栏里挖猪粪搬到田里,体力消耗实在过大,臭气熏天也不是美丽乡村可以忍耐的,因此,村民不再往猪圈铺稻草,而是直接用水泥硬化,粪便随时清理,清清爽爽。
人们养猪的目的,不再为了卖钱,只是为了吃到自己养的放心肉,再者,增加过年的味道。年底腊月,如果缺少了嗷嗷直叫的大肥猪,那是多么冷清的一个年啊。
但是有一个巨大的风险,像阴霾一样时刻笼罩在村民头上。年年都会听到传言,说某某地方瘟猪了。这让大家十分紧张,猪的瘟疫说来就来,防不胜防。
农民采取了很多朴素的办法。首先是给猪增加营养,提高免疫力。我的父母从来不吃牛奶,但是这两年回老家,经常看到墙边叠着的牛奶箱,原来是供奉给猪吃的。母亲还向我打听一些知名的营养品,这些他们自己是无论如何舍不得吃的,对猪却异常慷慨。然后是小心防范。村民之间互相走动,不约而同地不去猪圈,原本这是重点话题和重要交流现场,有客人来,尽量不让他们接触高贵的猪。全村养猪的人,都坚决不去市场买肉吃,他们担心买的肉,万一染上瘟疫,吃过之后,呼出的气排出的粪便,会让自家的猪遭殃。
父母一天需要做六餐饭,三餐饭给自己,三餐饭为了猪。给猪吃的饭必定占优先地位。他们自己吃的可以随便对付,而给猪准备的,必须有足够的分量和准确的饭点保证。周末我们回老家,妻子做好了晚饭,但是父母迟迟不肯来吃,去请他们,回复说必须等猪吃好了他们才能吃。
这些年,村里的猪,可谓集百般宠爱于一身。猪似乎与时俱进地意识到它们的价值和地位在提高,变本加厉地享受养猪人的溺爱。
父母说,今年养的猪,娇贵得很。倒在猪槽里的食物,不愿意自己去拱,得母亲用勺子一勺一勺递到嘴边。这哪是喂猪,分明是在喂孩子。邻村的叔父也觉得奇怪,他家的猪,散的猪食不愿吃,须得他用手捏成一个一个的团子才肯进食。他们村里,还有人做成饭团,一个一个递给猪吃。堂哥说,他家的猪爷爷,连玉米都不要吃了,番薯萝卜煮得稀烂,加点鸡精,才勉强张口。
猪一天天吃胖,主人除了劳动,还有时时刻刻的担心,直到摆好杀猪凳,烧好汰猪水,才放下心来,这时人已瘦了一大圈。
猪慢慢成了挑剔的美食家。不过它们的命运,永远不会是坐在餐桌边的主人,而是出现在菜单上的主角。父母、叔父和堂哥从来没糊涂:“我养猪,是为了吃猪肉,不是为了让猪幸福地生活。”
中国人吃猪肉的历史实在太悠久,《周礼·天官冢宰》曰:“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六牲即马、牛、羊、豕、犬、鸡,豕就是猪。天气变冷之后,我们家杀猪的事慢慢提上议事日程。父母总要征询我们的意见,什么时候杀猪?我们站在院子里,集体讨论这个事情。时间的确定,既难又简单,我们定了之后,还要看屠夫的时间。每年这段时期,屠夫的档期比明星还紧张。
冬至之后,再过五天就是腊月,阴冷的西伯利亚风把江南的气温压至零摄氏度以下。我在富春江边的酒店内参加一个盛大的婚宴,室内温暖如春,觥筹交错,但我心猿意马,等不及宴会结束,提前驾车离开。我在夜色中离开城区,驶向乡村。车灯把茫茫黑夜划开白白的口子,冲进更黑更冷的山区。
我惦记着赶回老家完成一个使命:抓猪尾巴。古人称猪为“豕”,“竭其尾,故谓之豕”。“竭其尾”就是翘起尾巴的意思。豕翘起尾巴为排便。所以我抓猪尾巴还是存在“被喷”风险的。在这场以多胜少瞬间结束的擒获战役中,父母其实没指望我担当主劳力,我却不能忘记抓猪尾巴的庄严使命。这是我唯一能使上劲,为父母养猪事业贡献力量的机会。
我去过嘉峪关,可惜没到过嘉峪关市东北20公里处的新城魏晋墓葬群,网络资料显示,那里方圆一二十公里的戈壁滩上,散布着1400多座魏晋时期的大型古墓,被誉为“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在一组魏晋画像砖上,刻画着当时养猪、杀猪的画面。猪圈前后,种有桑树,表明当时的人们也许已经懂得利用猪粪来让桑树长得更茂盛。杀猪的画面,与我亲身经历的农村杀猪场景已经非常相近。
屠夫今天安排不忙,下午还要去“麻将麻将”。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他留下来吃中饭。因为这餐中饭,我更新了对所谓美食家的看法,真正的美食家原来在乡村,在普通人中。把肉切成一块一块,摆在屠夫面前,他也能一眼分辨出这是哪个部位的肉,看得出新鲜与否。我想起苏东坡的《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我不敢把这首诗介绍给屠夫,他听了,一定会有不同意见。与其说苏轼是美食家,不如说他是哲学家。苏轼把佛学称为“龙肉”,把自己借鉴佛学而为我所用的实践态度比为“猪肉”。龙肉虽美,但虚无缥缈;而猪肉看得见尝得着。苏轼的高级,在于把猪肉作为了人生修养一种具体意象,形成了独特的“猪肉观”。
我想,他们都是美食家。屠夫和乡村的农民,可以说是前端美食家,他们注重食材,也有条件对食材挑剔。在我心里,这才是真正注重“吃”的人,他们对美食的理解,不注重花里胡哨的烹饪技法,而在最为关键的食材上把关,这才是美食的本质。除了味道,他们还十分有保障地注意了饮食安全。
我再去看美食文章和视频,他们头头是道地讲解厨房的玄学,殊不知如果食材不好,放了再多的化学试剂也无济于事。这一点清代随园主人袁枚还是认识到的,他在美食名著《随园食单》难得地提醒:“一席佳肴,司厨之功居其六,买办之功居其四。”他分享了采购食物原料时必须掌握的一些知识与技巧,比如“猪肉以皮薄为佳”。采办者其实根本无法从饲养的角度,评判猪肉的好坏。
即使是同样的绿色食物,猪吃热食和粮食,差别很大。吃凉食的猪,肠子上黏着食物;吃热食的,肠子上清清爽爽,自然味道更好。这与养猪人的勤劳程度紧密相关。
梁实秋在《雅舍谈吃》写到白肉时不解:“我母亲常对我们抱怨说北平的猪肉不好吃,有一股臊臭的气味。我起初不信,后来屡游江南,发现南北猪肉味是不同。大概是品种和饲料不同的关系。不知所谓臊臭,也许正是另一些人所谓的肉香。南方猪肉质嫩而味淡,却是真的。”如果那天中午,他在我家与屠夫坐在一起中饭,也就不会有这个困惑了。
我是家里的肉大王,逢肉便吃,父母辛苦养育的肥猪,一大半落入我的胃里。体检指标的异常,我毫不在乎。我认为,最好的肉味,是母亲在柴灶上热腾腾端出的红烧肉、腌菜肉、大蹄髈。我很奇怪,烧一碗肉,何必计较放几克盐几克糖,那种化学实验式的操作,与美味南辕北辙,美食不是技术,应该是艺术。要想吃得好,与其往肉里放多少调料,不如迟半小时开饭。
每年春节,我一定会到我的初中班主任家给她拜年,我的礼物从超市买来,大红的包装,喜气洋洋年味十足。我心里明白,这些大包小包,远远抵不上一块猪肉。《论语·述而》:“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意思是一束干肉,大约指十条干肉,是古代一种最基本的见面礼,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余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这是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表达,更体现对老师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