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中后期,中国广大农村全部实行了集体生产队建制,地处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故乡,更不例外。那时,各村屯、庄寨无一例外地成立了人民公社下设的农业生产大队,大队为最基层的一级政府,下面再以家族或紧邻的关系,组成若干个生产小队。
社会体制自不必说,农业上生产队多以种植传统的冬小麦和地瓜为主,这十分符合黄河中游地区的气候、地理的特点,本应无可厚非。
可那时的小麦单产量并不高,每年的收获,除大部分必须缴纳国家公粮,再扣除一些明年的种子,往往所剩已经不多,因此分到社员们家中的麦子寥寥可数,因此各家各户的农民都视麦子比较金贵,平时谁家也舍不得吃,好留做过年过节或家中有事有情时,做待客酬宾之用。
地瓜产量相对高一些,地瓜最喜欢黄河的沙土。亿万年来,黄河在这里留下了大片丰富的黄沙,为地瓜一展风采有了用武之地。地瓜比较耐旱、耐贫瘠,秧苗简单地插进沙土地里,到秋时结出的地瓜又大又甜,年年收成还算不错。也正是地瓜的产量,养活了黄河两岸广大的民众,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度过饥荒、度过困难,慢慢地走进今天社会的小康。
记得儿时生产队时期,每年地瓜收获之后,一部分就地分产到户,家家连夜进行切片,晒成白花花的地瓜干,这样可方便长久安全储存,是为一年的主粮。另一部分则必须窖藏鲜储,一来为储存地瓜种子,二来入冬以后,生产队每隔一段时日,取出一些分给社员们食用,使有限的食粮,发挥出最大最有价值的功用。
地瓜一般不需要充交公粮,储存得越多,保存得越好,年后春荒季节,社员们的口粮越能有保证,农民就心里就越有底。为此,故乡当地的每个村、每个生产队,都挖有储藏地瓜的大窖,并安排专职专业人员进行管护。全队人的希望,全体社员的生活基础,都压在管护员身上,他们责任十分重大,必须有经验、懂技术,还要积极负责、认真坚持原则。
地瓜含有人体必须的大量淀粉,鲜储存放时,部分淀粉会慢慢转化成生命所须的糖,因此,地瓜存放越久煮熟后越显得甜软。虽然地瓜吃起来口感不错,毕竟能量还是稍低,且难以长久存放,终比不上大米与白面。那时的中原地区,地瓜、地瓜干是农民们一年到头的主食,尽管不算难吃,但营养低、不抗饿,农民们都十分羡慕吃国家商品粮的人,他们的工作相对轻松又体面,且每月都有白面和大米供应,显得高人一等。
吃国家商品粮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大众还是农民。农民们必须以种地为业,必须想方设法下大力气搞好农业生产,好让小麦和地瓜等尽量获得丰收,这不仅仅是为国家做贡献,主要也是为了自家自己。谁都知道缺粮的日子,会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存。
农民种地比较辛苦,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风吹雨淋日头晒不说,还要靠天、靠地、靠技术、靠力气,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二
收获冬小麦,一般在公历的六月中旬左右,那时已接近夏至,太阳将要直射北回归线,带来日照时长,气温升高,中原地区天气极热。
俗话说“麦熟一晌”,晴天烈日下的麦子,集中成熟也就那么十多天,此时的农民最怕刮风和下雨。几天的阴雨,长在田中的麦子会发芽或霉变,刮一场大风能使麦穗互相摩擦,导致粮食脱落,这些都可造成丰收无望,甚至绝产,大半年的辛苦耕耘,希望就会落空。所以收麦季节最忙,必须抢时间、抢天气,至时学生们要放假,外出人员必须返家,全民老少齐上阵,就像打一场艰苦紧张的人民战役。
收过麦子的剩余产品,叫做麦草,俗称“麦秸”。传统收获麦子的方法,是人工用镰刀收割后,运至场院里集中暴晒,待干燥到差不多时,用牲畜拉动大青石滚子进行反复碾压,这样麦子的秸秆被压破压扁,麦粒自然脱落,然后再以传统的方式,分离出麦子、麦糠和麦秸。麦子是最重要、最精美的粮食,麦糠、麦秸可以做为饲草,喂养队里的耕牛等大牲畜。
翻开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长史,耕牛占有无比重要的一章,牛是华夏民族最亲密的伙伴和朋友。据说,中国人很古以前就开始了饲养牛等家畜,那时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为食物,直到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晚期,社会进入了铁器时代。铁器农具的出现,使牛这种力大无比的家畜,开始为人类服务,进行役使和耕田。此后的历史发展中,耕牛等越来越受农业所重视,这些大牲畜为中国农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当然,它的繁育、驯化和饲养,也是中国先民智慧的结晶。
中华古老的两河流域,为世界人类较早步入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特别是黄河地区,气候偏旱,人口众多,以致天然的饲草资源相对越来越加匮乏。既然农业离不开耕牛,饲草又难以满足,农作物秸秆被迫就成了饲养牲口们主要的饲草。
传承了千百年的麦收,饲养了千百年的耕牛,慢慢麦收后的麦秸,就成了耕牛无比重要的活命饲草。万古黄河造就广袤黄土大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华夏民族,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麦收,反过来人们用麦收后的麦秸,又饲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耕牛等。
生产队集体公有制时期,初期物质基础十分薄弱,耕牛越加显得无比重要。农业上的春耕夏作、秋收冬备,所有的繁重劳动,无不依靠着牛等大牲口,无不以畜力来减轻人力,完成繁重的劳作。
那时的生产队,为饲养这些大牲口,麦收后的麦秸,必须妥善保管,不允许有任何糟蹋与浪费。尽管当时社员们家中烧柴也都比较困难,但生产队决不能把麦草当做烧柴分掉,耕牛等是农业最重要、最得力的生产力,当时若没有这些大牲畜,丰收更是无望,农业更无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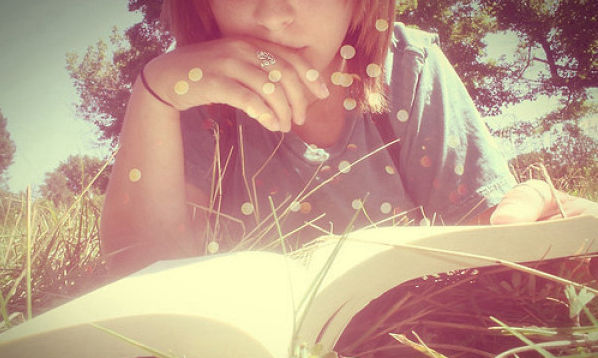
三
黄河流域种植的冬小麦,大约在每年的芒种季节收获,是时已近夏热多雨,万野处处葱绿。新下来的麦糠掺一些青草,正是耕牛们的最爱,所以麦秸为饲草的情况暂时用不上,只好集中起来加以保存,正如积谷防饥。
传统保存麦秸的方法,都是晒干后就近上垛,这样即可长期保存,又不至于被雨雪淋湿后霉烂,待寒冬和春荒时,保存良好的麦草垛,就是牲口们活命的粮仓。
上世纪集体化时代,堆麦草垛是生产队里重要的大事。为此,队长提前与队中的“长老们”磋商,首先选定吉日,然后开始准备庆贺用的食物。磨一百斤新麦白面,打十斤烧酒,买三五条低等香烟,再弄几斤糖果和一长串爆竹,这些都是必须的,条件好的村队还可能杀猪宰羊,弄些瓜果,但大多村队是到时候派人去队里的菜园中,采摘些新鲜的黄瓜、菜笋、韭菜什么的,拌两盆凉菜,炒几盘鸡蛋,最多再加一锅菠菜豆腐汤之类,将就着成事。
尽管食物算不得丰盛,但常年啃窝头、吃地瓜的年月,有一顿白面蒸馍或菜包子,还是相当诱惑人们的食欲,因此全队社员,男女老少都期盼着这一天。
悠悠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自古就把重要的事情体现在吃食上,小到百姓家的婚丧嫁娶,添丁贺寿及年节祭祀,大到帝王贵族家,先皇驾崩,新帝即位,出相入士和祭天礼地,甚至古时誓师出征、得胜凯旋,也无不以美酒佳肴,尽力搞好一场餐食活动,犒劳一下自己和招待宾众。定然喜庆事有喜庆的热闹,忧伤事有忧伤的规矩,但吃食无不力求尽善,活动无不力求尽美。
麦收大忙季节,是农民们最苦、最累、最紧张的日子。连续半月有余,必须没日没夜、披星戴月的抢收,的确很是辛苦。麦秸上垛,象征着一季麦收圆满结束,接下来的农事,相对少了些紧迫性,自然有了一时轻松感。这是一个时间段节点,放松一下喘口气,也在情理之中,况且一年一季的收成告一段落,收获多少暂且不论,付出过千辛万苦,小麦颗粒归仓,也算一次胜利,也应当值得举行一庆。
盼到既定吉日,只要天气晴好且无大风大浪,哪怕骄阳似火温度爆热,社员们都早早集中到打麦场。青壮劳力们把所有的麦秸摊开,厚厚地铺满整个晒场。几经上下翻动,让强烈的阳光烤干麦秸的最后一丝水份,然后套上几伙大牲口,拉动大石滚碌碡,做最后一遍碾压,一可使麦秸碾得更柔更碎,方便日后给牲口喂食,二还可以脱尽残留的小麦,以免造成浪费。
上午进行晾晒碾压,中午或下午才开始堆垛。主要劳力们操叉弄耙,把麦秸一叉一叉送上备好的土台,再由三两个年轻后生,站在垛堆上负责摊均踏实,像筑墙一样一层层地向上堆积。达到一定高度时,年龄大有经验的老汉们上场,开始以手撕眼观的方式,把外围不实的麦草整齐地薅下,修成上大下小、匀称、整齐、漂亮的蘑菇垛形。
为了安全和方便,各村各队的打麦晒场,一般设在村边地头且靠近大道的地方,麦秸垛高高矗立,过路人远远就能看见,因此麦草垛也是生产队的脸面,其大小和是否漂亮,影响着这个队的实力与社员们的农业水平。堆麦草垛算是全队人重要的形象工程,必须使出最大的本事,下足十分的功夫。
垛身有方有圆,上面一定要起弧隆顶,四周造出流水檐,环壁注意对称齐整。也许他们并知道“黄金分割法”,也许他们更不懂得怎样计算0.618的比值,堆垛全凭心目中的审美观,以双手创造成舒畅和协调的效果,这考验的是生产中劳动练成的智慧。
外表经过精修细剪,为防风防雨,垛顶上再抹一层光光的黏泥,至此堆麦垛的工程,算是大功告成。此时,其他社员也收拾好了场院,摆上预备好的食物与酒菜,全队人开始热热闹闹的大会餐。一时,洋洋喜气写在农人的脸上,欢声笑语回荡在四周的原野。
斜阳夕照,霞光射映,妇女和儿童们饱食一顿后陆续回家,只留下贪杯的男劳力还在场院中围坐,一边讲说着粗俗的传闻与小道消息,一边醉眼朦胧地评判新堆成的麦草垛,评判着刚刚完成作品的亮点与不足。
夕霞渲染,晚风吹凉,场院里消减了一些白天的燥热,村庄上空开始升起袅袅炊烟。田野如诗如画,麦草垛有如一幅美丽的剪影,劳累了一段时日的社员们,看着新筑起的麦草垛,就像画师刚刚放下手中的画笔,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这是他们心目中的艺术品,是亲自用双手创造的农村风景,无不感到畅快和自豪。
四
夏地瓜收获较晚,天时上大概已至老秋,农民的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而又重复着繁琐。大自然一年四季,年年传唱着人间的故事,也演化着天下万物的自律,农事作物都应时应节地甘为臣服,农民们必须跟随时节,慢度岁月。
因大自然天律约束,那时的反季农产品基本无法实现,春花夏雨,秋实冬荒,农人们靠着天时,依次走过了一个又一个二十四气。不像科技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今天,人类利用智慧,人为改造了自然,战胜了自然,才实现了部分反季农业生产的老梦,这是后话。
说起地瓜这种秧蔓植物,又名番薯或红薯,据史料记载,其原产地为南美洲的湿热带,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才由西班牙传入东南亚及菲律宾。在中国明朝万历年间,福建陈氏父子去南洋经商,初次接触到这种农作物,几经了解,甚是喜欢,联想到此物可解家乡粮食不足,救民于荒年,就决心把它引进回国。当时菲律宾处于西班牙的殖民地,他们视番薯为奇货,“禁不令出境”。于是,陈振龙精心谋划,“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并在外面上涂抹污泥,巧妙地躲过了殖民者关卡的检查,“始得渡海”为家乡引来秧种。
番薯传入中国后,大受人们欢迎,很快在全国广为传种。当传入中原大地时,人们惊喜地发现,地瓜尤喜古黄河留下的黄沙,感叹“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
地瓜“润泽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荠”,慢慢地红薯成为中厡地区仅次于麦子和谷米的第三大粮食作物。后有佚名诗人赋诗赞曰:地瓜“羞为王侯宴上客,乐充粗粮济民饥。”黄河地域历史上多灾多难,艰难困苦的灾荒之年,多亏地瓜做出了极大贡献,拯救了众多黎民,这些老辈人都深有体会。时光转到生产队时期,地瓜在中原大地上,早已深深扎下根,并不可推却地演变为生活主食。
记得那时的生产队,都种有两样地瓜,一是春种,一是夏植。春种的地瓜,是前秋预留的部分耕地,此地不播种小麦,闲置一冬后,春时翻耕,趁着湿土迅速插上提前育好的秧苗,等到麦收结束时,地瓜秧经已开始爬蔓分叉,长有二尺余长。绿油油的地瓜秧蔓,半掩了黄土大地,长势正旺,这时随意剪取一段,另插进新收完小麦,及时耕耘好的土地里,遇雨即可很快开长,此为夏季地瓜。
春地瓜种得早,生长期相对较长,下面结的地瓜也早也大,淀粉比较充足,中秋节后,人们就可以分期取食,以接济粮荒。等到田间五谷尽收,准备再次播种小麦需要用地时,春地瓜可以全部突击收获,然后分到各家各户,加工晒成地瓜干。
农谚云,“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中原地区的冬小麦,大都在秋分前后播种,届时所种的五谷正好成熟,必须全部收获,好与冬小麦让地,但夏地瓜却是例外,因为农民们预先归划,把它的地预留为明春早作物之用,所以不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