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量布尺子,是从爷爷那辈传下来的。听爸爸说,从20几岁就跟爷爷在染布房,学看布捻布调颜色手艺。解放后参加工作,在镇上百货商店卖布,时间长了在量布上掌握了一门绝活,镇上人都叫他-卖布老杜。百货商店改制后,爸爸承包了花纱布床子,又干起了他的老本行-卖布,我们兄妹三人成了他的徒弟。
每天,早晨8点30分,爸爸站在柜台前,把木尺子往肩膀头儿一别,看似十分威武,好像舞台上的冲锋将士,手握钢刀,肩插两棱,随时听令上阵,店门一开,尺子握在手中,亲切地面对顾客:“您好,请问选点啥布?”
爸爸笑呵呵,不慌不忙,摆好了架势,上下磨揉,开始量布。爸爸说卖布这活一头连着天,一头连着地,卖的是布,量的是心,不能欺人,坑人,良心要摆正。随手甩开布匹,赶开铺平,轻轻敲打兜起的坑洼包,用大拇指和二拇指捏着尺头,一把一把向前赶,另一手握住布中,心里默念尺数,快到看不到尺,布来回叠折,当量到尺数时,用剪刀一剪,刷地一下扯到底,不离不斜分毫不差,方方正正,叠好递给顾客。
量丝绸布料可不一样了,不能用手撕了,要小心地把布一把把展开,不搓、不捏,只有这样做出的衣服不打折,不缩水,量时需要顾客配合,两人各拿一头,到尺寸了,用力绷紧撕开,轻轻用火机烧掉露出的微细头,这才是一块好料。爸爸量的尺数与进货的匹数一点不差,业内人都夸,老杜尺头准,量得稳,分毫不差。在爸爸眼里,量布的活,眼睛要跟上,两腿要站住,臂力要使劲,两手要挥动,这样量出的布不紧不慢,有弹性。有时一站三四个点,想要歇个脚,只能靠在对面摆台一边蹲下,柜台不许吸烟,犯烟瘾含口水算解劲了。
“杜大爷、到我的啦!”顾客一阵叫喊声爸爸又站起来,接过顾客手里的小票开始量布。爸爸量布活,看似简单,一析一倒,匹数黙必记在心中。他精益求精,不差毫厘。在上下班路上,饭桌上他把手和筷子缠在一起,嘴里不停念叨一尺二……
上边下边直对角一致,反复练习这种手法。星期天,爸爸把家里几条毛巾连在一起,把眼睛用布蒙上,翻来覆去量一遍又一遍,妈妈说,你在班上没量够啊,在家里又折腾。爸爸心里一个梦想,量好布,练好手功。爸爸常说,布有时间、存放、季节性,能缩水能减量,卖布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这良心账,必须让人知道,不能坑人。进货选料是大事。
每次去天津大城市进货,爸爸亲自去,带着小本本,认真记录各厂家生产的布料使用功能,耐寒保暖降温纳凉的作用,凭视触摸各种布料。回来一有时间就去街头缝纫组坐一坐,跟裁剪师傅唠什么布料横竖纹利用好,什么潮式适合男女服饰,怎么做被褥不耽误材料,好多老主顾找爸爸给参谋,就连女儿出嫁、生小孩做衣服都问爸爸用啥布料好。爸爸说:“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能省就省点,别花冤枉钱。”那个年代,农村红白事情讲究用白花旗做礼物。赶上办事,哪家都买上百尺,大约五六木板匹数,爸爸都用尺量到一二百尺,中间不停手,肩膀酸乏,擦擦汗继续量,从来不嫌累。爸爸常说:不再多也得量,不量是‘存心不良,不能‘瞎扯’,公家不允许。”
晚上,爸爸一到家吃过妈妈做的热面条,急忙就躺下去,妈妈说,爸爸腰不好,爱睡热炕,我们就多烧几把干柴。后来,妈妈用海绵为爸爸缝做了一副腰垫,爸爸上班时带上,成了唯一的保健品。这一年,商场整合,扩大经营范围,我们由综合组变单项专营店,老邻居老顾客也跟过来了。
下来的布头,使用布料每次卖完,爸爸都攒齐着,卖给这些老熟人,并带她们到裁剪师傅那里做活。商场推行摊位经济效益承包后,爸爸花纱组讲成本核算。镇上一家农机厂老板找到爸爸要进一批布料做工作服,爸爸帮选宽幅又不能丢边料布,价格便宜,一些人不理解,咱也承包,干吗帮他算账。爸爸说,只图挣一时小利,留不住人心。第二年,工厂老板又来定做两季工作服。“老杜,我们信你,今后工厂福利事就在你们商场订货。”看见商场同行都用塑料尺子量布,我跟爸爸说:“咱也换尺吧,省工省事,一米顶三尺多好。”爸爸说:“来咱家买布人都认为这把木尺子,换了尺子就会丢了主顾。”尺子成了我们家王牌商标了。
一次,刚开店门,一位顾客气冲冲嚷着要退货,爸爸打开布一看一头是斜的,连忙道歉,重新测量了一块。因为那块布是我量的,见此情景吓得不敢吭声。“你要照这样量,给我滚回家,别干了。”爸爸大声训斥着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马虎了,量起布一是一二是二。有人问:买布的人都扎堆在你家了,老杜你咋不着急呢,还是一个劲地量,不怕顾客跑了。爸爸握着尺一笑说:“心里想着布,口里念着数,人不会跑的。”爸爸闲余时,总向我们传技,拿着尺子敲打布,用手摸布,他说,这能听出布的好次,验出布的松柔度。他还用彩块方搭各种颜色,调布料,爸爸说,时代不同了,要看街上人穿啥,咱就进啥布,这样才赶上时潮,提升年轻人审美观。童装是家长心仪首选项目,我和爱人拿着图形去幼儿园走访,回来和爸爸一起选料,并制作,小朋友得看着秋夏两款连衣裙跳高说,就选小公主裙。童装打开了我们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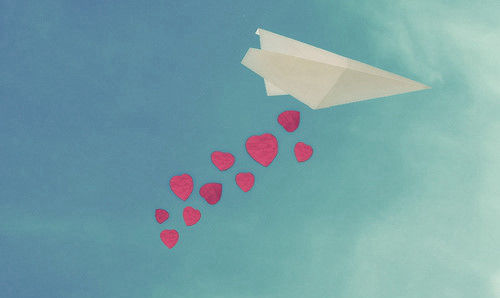
第三个年头,商场彻底解体了,我们拿着买断工龄的钱,闯进了市内最大一家超市,租了两张花纱床子,在爸爸的传授下,增加了品种,由零售走向批发,成立了“杜氏布料专营店”,风生水起,还参加了省内纺织学会举办的外贸展销会,爸爸被推举为市个体商会会长。专营店成立,在每年利润分红时,爸爸见到我们兄妹都喜上眉梢,个个探讨什么货时尚,什么面料流行,利大利小,就以董事长身份,要记住:生意兴隆,信誉第一,尺子是家风,根不忘记。有意思的是,在我们兄妹五个孩子中,我的小侄女报考了北京服装学校。她说:“我要跟爷爷学经销布,让咱家这份祖业传下去。”这一年,爸爸76岁了。在家庭会议上,他又了强调说:“我老了,这把尺子交给老大,尺子是帅,谁主帅谁当家。”约法三章:量布要有良心,卖布要让三分,价格要不超利。每年以3%利润,做爱心活动。爸爸这一举动,推动了我们市爱心助教事业,后来在滨城一直流传布王助学的故事。
爸爸的尺子像家乡那座沧桑古老桥的背脊,在坚固铸起做人的情怀;爸爸那把尺子又是我梦中,闪烁星光的月亮,在照耀我和家人;爸爸那把尺子又像游走天下的卖货郎,叫买一个又一个顾客,量出春色满人家。爸爸的布尺子,是时代的火种,在传递和发光着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