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下万物皆生于有,而有则生于无。
如果我们执意要追究泰山的出处和身世,单靠请教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或考古学家都没有用,因为他们一开口,就是大约28亿年前到25亿年前之间,这一“大约”就“约”去了3亿年,这显然是拿“亿”这个量词不当回事。如此巨大的空隙让听者如何去填补!如此遥远的过往让今人如何去感受!
所以,我们不如去发挥我们该有的听力,顺空间上升,逆时光而行,穿越无垠的苍茫,去仔细谛听25亿年前,因地壳剧烈运动而产生山崩地裂的那一声轰然巨响。甚至,我们还可以忽略掉泰山在大地母腹中那长达20多亿年的精心孕育,而只需将听力延伸到4000万年前,倾听泰山拱破大海的“羊水”后,横空而出的那首生命之歌。那才是大自然真正的命运交响,那才是天地间最为纯净的动人旋律。
那一刻,不是泰山在等待着看日出,而是出日在观看着泰山如何地升腾。
那场景,想想就很奇妙。那画面,想想就很震撼。

天地作合,万物生长,泰山已经成长为了泰山的模样。4000万年前,世界的东方,一座苍莽大山,年轻,巍峨,厚重,浑然!
泰山高吗?高,但不是最高。泰山大吗?大,但不是最大。但却唯有泰山,拔地通天,可以供人君与上天对话;唯有泰山,斤两最足,可以称得出生命轻重;唯有泰山,祥云最稠,可以招徕众仙汇聚;唯有泰山,风调雨顺,可以昭示国泰民安。
更有传说,盘古死后,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右臂为北岳,左臂为南岳,足为西岳。在东方这太阳初始的地方,按“五行”属木,按“五常”为仁,按“四时”为春,按《周易》属震,按“二十八星宿”为苍龙。单是一个繁体的“东”字,也能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会有日出扶桑之说。
如此,泰山进入“五岳”是必然的,在五岳中独居尊位也是必然的。这一点,极顶上那块25亿年前的岩石,上面写得清楚:五岳独尊。每个字都是半米高大,生怕观者看不清楚,防止他们一不小心把头偏到天外去。所以在“五岳独尊”一边,专门标注了四个字:昂首天外。
用脚去丈量泰山,显然太笨拙太费劲。用情去包裹泰山,显然太单薄太轻飘。用心去感悟泰山,显然太博大太沉重。其实最管用的方法,就是自己长成一座山,跟泰山站在一起,天涯共此时,相看两不厌。
二
但有多少人能够自己长成一座山呢?
有多少人登上泰山,就会有多少人从泰山上下来。这其间,好像只有一个人是例外。
公元前557年,66岁的叔梁纥带着不满20岁的颜徵在来到了尼山,6年后,60公里之外的泰山听到了一声婴儿的啼哭。
白云苍狗,眨眼之间,这个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的年轻人已成长为一个学问家。他博学好问,创办私学,思考和传播社会之“礼”和人性之“仁”,钟情于等级和秩序,希望弟子们能够“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但乱云飞度的春秋仍然让这个年轻人不时地迷茫,除26岁那年请教过郯子以外,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可以问询的人。
孔子应该是带着满腹的疑问登上泰山的。当他站上泰山极顶,他才知道,他所心心念念的天下,在泰山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泰山岩岩,鲁邦所瞻。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则小天下。
山顶上,他站过的地方,已经成为瞻鲁台。长风吹过,白云飘过,泰山无言。面对万千风景,孔子想的是,如何解开“救世”情结,如何展开“入世”情怀。问天下有没有王权,能不能施行仁政,礼崩乐坏的糟糕局面能否得到扭转,那让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如今还好吗?
无论是前往泰山还是从泰山上下来,孔子都要经过大汶河这条世界东方最大的倒流河。倒流的大汶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水中同时晃动着鲁国和齐国的倒影。
子路、子贡、颜回、仲由、公冶长、冉求、言偃、闵损、宰予、司马耕……这是一串很长的名单,孔子带着他的这些弟子们,一次次从河面的小石桥上经过,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一个个心怀天下,直到把桥面上的石块磨得油光锃亮。在形成齐鲁两强过程中的四十多个小国,有不少都曾在这座小石桥上滑倒过。
当年齐国送鲁国的八十名美女,也是从这座小石桥上经过的。美女们把河水当成镜子,满河的水一度驻足,不愿流淌。孔子想挡住这伙人的去路,但却挡不住。之前,他也曾劝过季桓子,却根本劝不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鲁国从此开始上演奢靡沉沦的歌舞剧。这让孔子十分地失望和伤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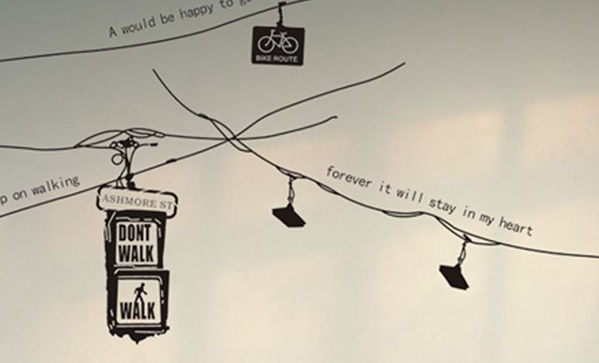
思想者注定是内心孤独和备受煎熬的,登顶泰山并没有给他带来轻松,而是给了他更多的沉重。周游列国的14年,他和他的弟子们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常落魄如丧家之犬。但这并非孔子的刻意为之,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因为不管现实再怎么满目疮痍,但他还是始终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信仰,大同社会,大道畅行;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充盈着仁礼义信的小康生活早晚会到来。
正是因为心中有着稳如泰山般的坚定,他才可以一边知着天命,一边耳顺,一边从心所欲地修订出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泰山还是一座自然的山,地理的山,封闭的山,它有着端庄流畅的造型,四季分明的时令,充足的阳光和雨水,陡峭的崖石和长长的盘道,茂密的松林和潺潺的清泉,绚烂的鲜花和多彩斑斓的蝴蝶,青嫩的草丛和快乐的小鸟,漫天的祥云和全新的空气。那么在此之后的泰山,则已经真正开始生长文化的青苔,并向着一座思想的山、哲学的山、历史的山、文明的山、开放的山进发。
也就是说,孔子人从山上下来了,但他的思考和学说却留在了山上。他是一个与泰山齐高的人,一个在当世就被奉为“天纵之圣”的人。
他的建造儒学文化大厦的构想,毫无疑问是从泰山脚下开始生发的,他也毫无疑问是当然的奠基人,后来是孟子备足了料,是董仲舒建成了毛坯房,是王阳明进行了精装修,是孔子学院向世界打开了一扇扇东方文化的小窗口。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圣人就是圣人,几句话就准确地概括了自己伟大的一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这个“川”,我们就设定它是从东向西湍急倒流的大汶河吧。
河水倒流也许并不稀奇,如果时光能倒流,那才珍贵!
三
道,可道,非常道。
从没见过一部书有这么简洁、深邃、锐利和充满哲思的开篇。仅仅5000言,就包容了宇宙,包容了天地,包容了万物;就包容了修身之道,治国之道,用兵之道,养生之道;就看透了本源,说清了物理,悟彻了人伦,达观了世事,清明了人生。
《道德经》,这部老子的著作,成为了《圣经》之外,翻译文字最多的作品。
这样的人,是孔子迫切希望能见到的。
公元前535年,鲁国巷党。公元前518年,周都洛邑。公元前498年,沛。又过几年,鹿邑。这些时间和地点,都与两个人有关。他们一个叫老子,一个叫孔子。对于他们之间的见面,后世给出一种很雷人的说法,叫火星撞地球。
他们之间到底是见过一次,还是见过多次,至今仍然存在很多争议。其实,见过几次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见过。
他们两个人的身边,一会儿是槐树,一会儿是柏树,一会儿是楸树,一会儿是杨树。地点不同,景色自然也不同。
他们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个年长一些,一个年轻一些。一个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个重礼,一个说礼只是工具。一个尚仁,一个认为仁的概念太宽泛太模糊。那个年纪长一点的说,人啊,再聪明也要少非议,懂得再多也不要动辄教训别人,真正有钱人应该让人看起来像个穷光蛋一样才行,真正有修养的人应该让人看起来像个傻瓜一样才行。总之,为人处世要知敬畏,毋以有己。
他们像极了两个空手道高手,云山雾罩,不着边际,契阔谈宴,两潭深水。他们对话的声音并不高,但却因内容的敏感和深奥,在略显荒芜的大地上引发出了一阵阵宏响。他们自己也并未想到,自此以后,两条思想的大河便在东方大地上,开始了沧海横流,不仅成为一个国家思想史的原点,也成为了世界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华章。
高手之间的过招,往往表面朴实无华,背后却流光溢彩。
相见后,弟子们问归来的孔子,什么情况?孔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视老子为神龙,说明孔子心里很服气。
泰山记住孔子,毕竟孔子登上过泰山。老子虽然到过鲁国,但却并无登上泰山的记录。如果说孔子登一次泰山,其眼界便从此悬挂在了泰山上,那么老子根本不用登泰山,泰山便会自动成为《道德经》最好的标本和注脚。泰山,是“道”的最佳道场!
泰山脱胎于自然而融入自然,静极,无为,不言。利万物而不与万物争,坦荡,刚强,雄阔。因不自大,而成其大;因不自生,而能长生。人应如泰山,内心宁静,心境超脱;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内敛沉稳,自胜者强;活而不昏才是最大的智,死而不亡才是最大的寿。既然来是偶然,去是必然,那么中间这段最好的选择,无非是走近自然,亲近自然。小国寡民就好,不要纷争,更不需要战争。
一个“道”字,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论三生万物,还是道法自然,它都涵盖了天地间的物理、精神和规律。所谓的玄之又玄,其实一点都不玄,不过是至简至易,清新明了。
由此,泰山记住了这个“身长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长着一副大耳朵的人。
大音希声,但一副大耳朵,足以让他什么都听得仔细,听得分明。
传说,是会观天象的函谷关关令尹喜,提前做足准备,将倒骑青牛准备出关的老子,堵在了关内,并以“圣人者不以一己之智窃为己有,必以天下人智为己任也”为说辞,成功将老子滞留在关内数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了这个天下著作最经典的起首,老子也就刹不住车,也无须乎再刹车,而是一气呵成,完成了尹喜所要的作业。“道”篇37章,说透宇宙之根本,之变化,之玄妙;“德”篇44章,言明处世之方略,之进退,之长生。鉴王朝兴衰成败,纳百姓安危祸福,总言5000余字,已经够了。
很难想象,如果老子是在泰山上撰写《道德经》,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如果老子出关后,不是去了老君山,而是去了泰山,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四
有了“道”,泰山便不止是一座圣山,更成为一座仙山。
神仙们喜欢在这儿居住,想成仙的人喜欢到这儿来修炼。
在泰山上住过和曾经住过的神仙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只能说天上有多少颗星,泰山上就有多少个神。传说,泰山犄角旮旯里都藏满了神仙,那些没有具体住处的只能挤在同一座小楼里,“万仙楼”便成了这座楼最合适的名字。
这么大一座山,这么多神仙,得有一位“管理”者才行。“管理”泰山的是一位女性。一说碧霞元君,听上去很尊贵;一说泰山老奶奶,仿佛年龄有点偏大;一说泰山娘娘,感觉上好像才秀美了一些。其实,这说的是同一个人,是一个人的不同叫法,是她的正式仙名和不同的民间爱称。
雄伟的泰山由这么一位端庄秀美的女性来“管理”,或许也正应了“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说。
严格说,在碧霞元君之上,还有个“一把手”,那就是东岳大帝。但仅从他们的“办公地点”上,便能看出一点错乱的端倪。东岳大帝常驻岱庙,岱庙在山脚下,被公认是登泰山的起点。而碧霞元君的住所兼办公场所碧霞祠,却是居泰山极顶,距玉皇庙咫尺之遥。
按泰山容三重世界说,岱庙周边为人间烟火,奈河以西的蒿里山地下为阴间地府,一天门之上为仙界。本该“一把手”的东岳大帝,并非一览众山小,而只是“分管”了“死”这档子不被待见的事,而且“业务范围”与执掌阴曹地府的阎罗王的职责还有点重叠。本属“助理”的碧霞元君,反倒成了“执行董事长”,高高在上,无所不管,无所不能,无所不美。
神仙们有聚会的,有下棋的,有炼丹的,泰山赤灵芝也常以可爱小红孩的形象四处游走,但这不妨碍鲁班在这儿建观筑庙,不妨碍华佗在这儿采药熬汤,不妨碍王羲之在这儿题词留墨。也不妨碍雷雨天陡峭的岩石上突然长出茶树,不妨碍晴天丽日下坚硬的崖壁上突然跳出白羊,不妨碍暗夜的幽幽深潭之中突然飞起黑龙。更不妨碍秦朝的松仍在强势地生长,不妨碍汉代的柏仍继续加剧着盘根错节,不妨碍唐代的槐仍于风雨中翠绿着枝叶。
同样不妨碍的是芸芸众生的上上下下,来来往往。
登上泰山的更多不是名人,而是凡人。第一个登上泰山的人肯定不是孔子,甚至也不是炎帝或黄帝,不是伏羲也不是姜太公,不是周天子也不是他的长子伯禽,而一定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这就像泰山上长出的第一棵树是什么树,泰山顶上飘过的第一片云是什么云,泰山上飞过的第一只鸟是什么鸟一样,根本无从考察,也无须考察。一天门,中天门,南天门,仙界也是有层次有级别的,踏入仙界的门槛或许并不高,但真正能成仙的却是少之又少,甚至是世所罕见。并非过了升仙坊,你就会自动成为了神仙中的一员。但攀登一次泰山和从未攀登过注定是不一样的。
人们把泰山主“生”,移植到了碧霞元君身上,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女性和那些结了婚而想要孩子的女性,她们最愿意跟碧霞元君攀谈。只是攀谈的姿势,她们习惯于跪着。
泰山极顶,碧霞祠。这座典型的道教模式的古建筑群,背倚巍峨峭壁,前面万丈悬崖,端庄疏朗,大气磅礴。祠内南神门上层的戏楼,是专为仙乐仙舞的演出而准备的。凡俗的人是很难有眼福看到的,但想必碧霞元君可能也顾不上观看,因为求她的人实在太多,一天到晚总是排着长队。要问天底下谁是救人最多的人,那一定是碧霞元君,这也是泰山给出的答案。因为她只做好事,从来都是雪中送炭,给有难者以帮助,给有求者以呵护,给卑微者以希望。
泰山可能是唯一一座没有旺季淡季之分的山,而且泰山也很可能是唯一一座要来就来两次的山,除非第一次时你没有留下任何心愿。
五
与泰山石打交道最多的,当属泰山挑山工。
沉稳的泰山挑山工,一向不显山不露水,总是在你不经意间满负荷地到达极顶,然后一身豁达,这从中已经给予我们太多的人生哲理和生活启示。你可以说,他们每天的工作都是重复的,可这世界这人生定然充满着太多的重复,不是每一种重复都是毫无意义的。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是结果重要,而是过程重要。这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深奥的人生课题。所以,对泰山来说,举办国际登山节一定很有意义,但如果举办泰山国际挑山节,意义也许更加重大。
常年累月,泰山挑山工的脚几乎与泰山上的石头长到了一起。他们用脚,坚硬了岩石,陡峭了盘道,抬高了意志,升华了胸襟。一条刚中有柔、柔中带刚的扁担又几乎与他们的肩长到了一起。他们用肩膀扛起了大山的使命,扛出了人生的壮丽;他们用扁担,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挑过了远远超过泰山的重量;他们用汗水浇灌了泰山葱茏茂盛的万千植被,滋润了泰山绚丽多彩的千古传说。他们的脊背常常是裸露的,一如泰山敞开着胸襟。呈现出的古铜色,映着沧桑历史之光。他们健壮的肌肉,线条分明,一块一块像坚硬的岩石一样隆起。他们的两腿早已锻造成两根粗壮的石柱。
每一包水泥,是他们送上去的。每一袋沙子,是他们送上去的。每一块青砖,是他们送上去的。每一样蔬菜,是他们送上去的。每一道食品,是他们送上去的。
2000斤的索道驱动轮,是他们送上去的。3500斤的中天门大钟,是他们送上去的。4000斤的索道液压缸,是他们送上去的。4000斤的气象雷达底盘,是他们送上去的。一米45斤重的缆绳,是他们送上去的。6000斤的大绞盘,是他们送上去的。6000斤的发电机,是他们送上去的。7000斤的空压机,是他们送上去的。8000斤的油压轴,是他们送上去的。
在这里,只有顶天立地的泰山挑山工。
青山依旧在,人间几度秋。这个把握是对的。
如果说,我们必须用一首歌,来唱出我们心中的澎湃,那只能是《我们是黄河泰山》:“我登上泰山之巅,天风浩荡向我呼唤。中华的风骨像泰山千秋耸立,铭刻多少功绩,多少荣耀,多少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