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小消失八年,再见面,我已回到家乡,一座北方古城,经营咖啡馆。基本是赔钱买卖,凭父母给的费用维持着。拆迁后,父亲开始做建材生意,越搞越红火,人都油光起来。他按月给我打钱,说,啥时候玩腻了,就跟着他干。
古城旅游不景气,大部分商铺都在勉力支撑。隔壁原先是手工艺店,卖布偶、陶人和手工璎珞之类。店主姓林,我叫她林姐。林姐比我大几岁,人很好,爱笑。她教会我打手鼓,作为回报,我在她店里购买了很多捕梦网风铃,用作咖啡馆进门悬挂的装饰。林姐在古城待了三年,临走前送给我很多小玩意。
我一个人,吃住都在店里,城外的房空置着。买房时,父亲出钱,咬定要买大面积,没考虑我独自住,太冷清。店铺进门左手,有隔间,是我的卧室。落地窗临街,地上摆放花盆,月季,红海棠,还有我最喜欢的夏菊。游客旺季,我会采摘几束,插在餐桌上的白陶瓶里。有时不留神,花束不见了,我懒得管,少了再去添一束。我用白漆在木板上写,客留随意、勿扰他人,然后钉在大门上。
女友读研,放假来找我,也住店里。户部巷生意寥寥。女友问我,为什么不在主街上盘家店面。她看向窗外,小巷了无行人,晚阳直直地铺来,遇不到丝毫阻碍。我喜欢户部巷的风景,它不工整,临街店面瓦檐残缺,门框没有刷统一的红漆,没有挂同款的商旗,这让我感到心安。晴朗的早晨,我可以倚靠窗边躺椅,看阳光慢慢铺过青石砖,再睡个回笼觉。我回答她的是另一个理由,这里安静,人少但是不忙。
租金也低,我补充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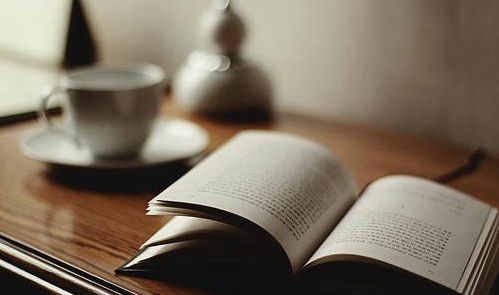
女友点点头,好像总能理解我。
范小小推门进来,我正低头串珠,心想多串些撒在鱼缸里。圆珠的孔隙太小了,每次穿线都很费劲,眯眼皱眉,好不容易塞进线头,手一滑,珠子啪地掉落。
抬头。她站我面前,掩着嘴笑。
我问,要喝点什么。
她不说话,睁大眼睛看我。
她的眼睛好看,似有灵物,吸引我也看她。越看越狐疑,越惊讶,也越熟悉。我看她的脸,还没想起什么,直到她的卷发传来清淡的橘皮香味。我跳起来喊,范小小。
串珠蹦落,在地板上跳跃。范小小笑着说,看来还记得我,没忘嘛。
我不会忘记她独特的发香。它和长方砖台下的千头菊、石桌旁的橘子树,共同构成了我对一个院落的记忆。小小有独特的洗发秘方,她收集橘皮,洗净晒干,等待变成陈皮。她用陈皮泡水,红白纹脸盆置在砖台,低头,长发沾水,白净的脖颈暴露日光下,像涂了淡金色的腻子。陈皮在水盆里晃晃悠悠,清涩的香气跟随漾动。我看到气味像水,镶了金边。
她伸手说,帮我拿毛巾。
我和文江就拽着一条毛巾,塞到她掌心。
现在,她穿露肩碎花长裙,挎着白色针织包,人和那时一样清爽,更好看了。
我曾有许多疑问,她为什么不辞而别,文江为什么要锯倒那棵橘树……这些事文江从没告诉我答案。它一直鲜明地摆在那里,指向文江,指向小小,也犀利地指向我。可见到她,回忆反而淡漠,疑问像水泡一样破散了。
我递给她咖啡,请她坐下,正寻思如何开口。她手指身后,示意来了游客。戴红色旅游帽的中年大叔踱步进来,四处闲看。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开店。她说,缘分,本来打算闲逛,一扭头,看到你在串珠。我挠挠头,珠子还在地上散着,像过去的日子一样零碎、散漫。她说,你没变化,我一眼认出来,差点吓一跳。我说,你也和以前一样。她笑笑说,是吗。又问,开店几年了。我说,四年,大学毕业就回来了。她微微点头,犹豫片刻,抿一口咖啡,拿起桌边的手账本,随意翻看几页,说,蛮有意思。我说,没别的,就想听听别人的故事,觉得自己活得挺那啥,说不清楚。我继续说,你看这个,烤鱿鱼串的小尧,和银饰店的涵哥,两个人有过节,他们在手账本上以记录的形式对骂了十几页。那些天,我的收入稳定。小尧中午来,点一杯拿铁,坐着写,洋洋洒洒,咖啡很快下肚,他走后,涵哥立马到了,他先批评拿铁的无趣,然后品咂着冰美式,写得字斟句酌而洋洋得意。两人的争论为后来的游客提供了乐趣,他们分析辩驳,那十几页不大的纸,很快写满了纷纭的意见,再往后便无处下笔。兴致盎然的游客不知当事人早已和好,他们矛盾的起因大概在于涵哥嫌弃小尧烤的鱿鱼串难以下咽,而和好的动机是因为小尧想给他女朋友打一对银手镯。
